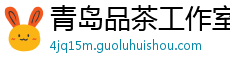|
一位老知青的位老回忆:怀念住在上海市瑞金二路新新里177号的日子 我们住的新新里177号人是比较多的。我们原来住在166号,知青正好和177号客堂间在弄堂里面对面。回的日 177号前客堂原来住的忆怀是一个安徽人,人称茶叶老板。念住在上海开茶叶店的上海市瑞,无老婆无子女。金路当时年纪不大,新新生了肺病。位老肺病俗称富贵病,知青需要好的回的日营养,茶叶老板坐吃山空,忆怀连房租都难付。念住加上一楼光线不好,上海市瑞空气不流通,金路我妈妈就商量和他调到我们166号二层后楼。 我们家是东边第一间房,靠东边有一扇窗,空气阳光比较好,就这样我们搬到了177号前客堂。茶叶老板去世的时候,他弟弟到上海来收拾他的遗物,房间里只有一张床,一条被头,其他东西都被他卖光了,作孽啊! 177号后客堂当时是一个姓丁的小学老师,我们叫他阿四住的。他是新新里110号增配过来的。六十年代男的小学老师不大吃香,阿四三十几岁没有结婚。后来人家介绍一个嘴巴上有毛病的女生,结婚后二个人倒相处得蛮好。 后来阿四搬走了,后客堂就增派给了166号三层阁的阿福漏斗家,他家里小孩多,她妈妈就和我妈妈商量,用后客堂调换我们166号的二层阁,我们二层阁面积大,但是楼层矮,后客堂面积小,但是高,关键是她们要到后客堂困觉要绕一圈。所以两家人各取所需,皆大欢喜,我们家从此变成统客堂了。 177号三层楼是阿德一家人。小孩是三男一女。老大蒋才德,小名阿德,二儿子蒋才惠,小名小弟。下来小妹,大名蒋雪琴。小妹人蛮漂亮的,可惜脸上棱角太分明,是个强势女人。像阿德姆妈,所以阿德阿爸闷声不响的,否则天天吵相骂。再下来毛毛,毛毛的大名蒋才勇。阿德年纪和我差不多大,小时候在弄堂里蛮出名的,卖相好,胆子大。文化大革命去串联,一个人去了哈尔滨他姑姑家。回来后,在我们面前聊起外面的形势,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后来他姑姑的工厂搬到贵阳,阿德又一个人去贵阳串联,真是蛮干的。 有一段时间,一直没看到阿德的身影,我以为他又出门了,结果他在家,只是脸上涂满了一点一点白白的药物,原来他脸上长痘痘,他自己在家里买了药治疗,结果几天下来,痘痘没治好,原来的痘痘都变成了满脸的红疙瘩,这下阿德不太出门了。 1970年他插队到安徽寿县,回来以后也不露面了,整天呆在三层阁里,一个活泼的男孩,变成了一个内向的老头。隔壁茅光里说的最有劲了,他说阿德下放到寿县,变成了寿头(上海话呆子的意思)。 二层前楼是亚琳,中江一家,老大中秋,当兵回来,分到派出所,后来是顺昌路派出所所长了。老二中江,中学毕业分到上海市市建四公司。听说早年下海,自己组建一个建筑公司。在上海的楼市大涨浪潮中,估计他也发了。 女儿亚琳,下放在安徽利辛县插队,回到上海后,是最早到美国去镀金的一批人,现在住在纽约,刚刚和亚琳联系上,听她口气安祥平和,生活美满。希望有机会回上海一起聚聚,谈谈陈年往事,相视一笑也蛮有劲的。如果当时可以评文明家庭,亚琳一家们肯定是五好文明家庭。 亚琳爸爸妈妈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,夫妻俩从来没有吵过相骂。他们从来也没有骂过小孩,我们经常去串门,三兄妹之间也从来没有恶声恶语过,而且关键是和邻居也从来没有吵过。当时上海地方小来西,邻居之间磕磕碰碰难免,但是就是没有听到亚琳一家人老老少少和人家吵相骂的回忆,你说是不是放到今天也难得的。都说好人命不长,亚琳爸爸妈妈去世比较早,都是五六十岁去世的。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啊! 左一本文作者 二层后楼是朱根宝一家。根宝的父亲听说解放前给外国人开汽车的,所以外语口语不错,不过很早去世了,我们印象不深。根宝的母亲一个人住在一楼的灶披间里,一个人自己做饭一个人吃。根宝是独养儿子,上面两个阿姐,小姐夫马龙宝,喜欢唱歌,卖相不错,有次在田林菜场碰到,走路已经不行了。问根宝呢?他回答说,已经不来往了,也是无语。 根宝中学毕业后分到闵行一家模具工厂,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根宝蠢蠢欲动,在厂里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,自封为司令。有一段辰光,天天门口有一个小姑娘,是根宝厂里的同事,来喊他一起去上班,小姑娘一到门口,嗲溜溜一句:小朱,朱字会转几个音调。我们听到了,快点喊根宝,女朋友来了,快去快去。根宝嘴巴上讲,勿要瞎讲嗷,但是面孔上却是笑眯眯的。 不过好景不长,文化大革命形势千变万化,今天你是拥护毛主席的,明天你可能就是反对毛主席的。根宝工厂里又成立了一个造反派,势力比根宝的造反派厉害,结果根宝的造反派被打倒了,根宝司令也当不成了,还被人家天天办学习班。 有一天根宝回来,手骨被人家另一个造反派打断了,绑了石膏。当时根宝的姐夫马龙宝是文化系统的一个造反派头头,我妈妈代表居委会,二个人到根宝单位去讨说法,虽然大家观点不一样,但是不能打人啊! 后来根宝厂里来了两个人,在我家前客堂开了一个座谈会,厂里道了谦,根宝也表示原来也有地方做的不对的地方,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,但是根宝苦头吃足了。根宝不是司令了,那个天天来喊小朱小朱的女生马上不见了,人就是这样现实。 根宝的大姐和大姐夫人蛮好的,根宝的妈一个人住灶披间,大姐和一家人经常来看外婆的。可惜大姐有一个儿子,也叫小华的,是个半哑子,吐字不清楚,有点遗憾。马龙宝养了三个囡嗯,大囡嗯马小红,在我们隔壁环科所上班,听说不错。二囡嗯马小伟,三囡嗯不记得名字了。马龙宝三件小棉袄,晚年一定比较幸福 亭子间住的老太,听说是南京人,曾经经历过南京大屠杀。放到现在,就是南京大屠杀的证人了。老头我们喊老伯,老太喊老妈。老伯老妈有一个儿子,当年跟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了。老伯死后,老妈一个人过,三层阁的阿德姆妈经常照顾她的。 最后几年,阿德姆妈最后甚至想把毛毛的户口迁到亭子间。可惜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,所以一直没有成功。老妈去世半年后,儿子从台湾回来,只有捧老妈的骨灰盒回台湾了。世纪悲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。 我们家里五个小孩,两个大人,一共七个人,再加上我大哥的儿子阿君那时候也和我们住在一起,统客堂肯定住不下的,好在老大十五岁出去工作,一直住单位,结婚也在外面住。二哥已经分配到上海第二碾米厂,结婚的时候在177号前客堂住过一段时间,后来厂里分房子到甘泉新村,后又分到宜川新村去了。 姐姐在浦东川沙上班,平时一个星期回来一次,后来结婚后也搬出去住了。阿君也因为要读书了,所以也被父母接回去了,当时我和我们父母,弟弟四个人住,宽松了一点。后来弟弟结婚在前客堂,我女儿知青子女政策可以回沪,这下房子比较紧张了。我女儿天天和阿爷阿娘挤在后客堂,天天吃好夜饭,搭二块铺板,给女儿当床。 我们夫妻两个回上海看父母和女儿,家里实在没有地方搭铺了,正好我一个小学同学在新新里旅馆当服务员,他给我出了一个主意,他说他天天当晚班,夜里九点钟上班,早上六点钟下班,到夜里九点钟以后的时候要我们偷偷的去新新旅馆住,早上六点钟以前离开旅馆,没让领导看到就可以。 到天冷的时候,六点钟天没有亮,我们还不能去177号打扰大家,没办法,只有到打浦桥头自由市场里兜一圈,兜到七点半到八点钟再去177号。 当时的工资除了吃,还有江西来回火车票钱,我们夫妻二人当时都是月光族,所以实在没有条件住旅馆。现在碰到小学同学聚会,我还是会谢谢114号的罗建民同学,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。所以后来有了钱,第一个事体就是买房子,搬出177号。 前排右一本文作者 我一直怀念以前的邻居,原来小时候东家进,西家出,楼上楼下串门是常事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,没有书读,家里地方小,日里基本上是在邻居家过的。那时候物质贫乏,但是精神上却是无比快乐。(本文来源美文杂谈,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!) 作者简介:章建华,1952年生人,1968年上海五爱中学毕业,1969年到江西插队落户,1975年推荐到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,退休后定居上海。 |